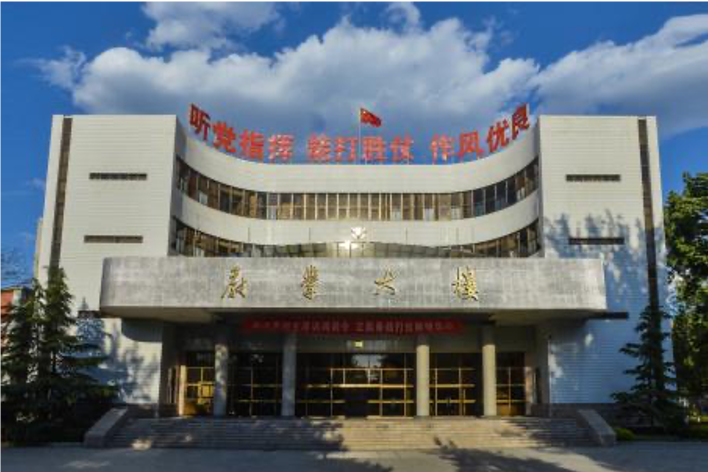一部电影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由他们决定
2024-06-27 次
一部电影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由他们决定在电影创作的世界里,分镜画师是其中一类“深藏功与名”的幕后英雄,他们与导演密切合作,最先将剧本中的文字“翻译”成视觉画面,供整个拍摄团队参考。其实,分镜本身也是一种独特的、具有美感的艺术形式,但分镜画师们的使命在于视觉传达,即讲故事,设计分镜时需要考虑一场戏的构图、运动、镜头角度、特效和节奏。而且,这些“草稿”往往历经反复修改,无法得到妥善完整的保留,又或者终被积压在库、永久封存。
《电影分镜艺术典藏》难能可贵地将分镜的价值公之于众,作者费奥纽拉·哈利根(Fionnuala Halligan)以其备受公认的行业影响力、全球化的卓越视野,竭力搜寻四处散落的档案,沟通错综复杂的授权,精心编选展示了一系列风格各异、时代各异的分镜画稿,包括许多伟大电影的精彩时刻。例如,威廉·卡梅伦·孟席斯(《乱世佳人》)和索尔·巴斯(《惊魂记》《斯巴达克斯》)等先驱大师们的罕见手稿,当代分镜巨匠劳尔·蒙赫(《潘神的迷宫》)和简·克拉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的精美画作。当然,还有更多首次披露的分镜画师及其画稿,创作思路、幕后故事与作品赏鉴。
这是电影历史的“时间壁画”,也是电影艺术的“幸存品”。无论对影视动画、美术设计、广告游戏领域的专业人士,还是对影迷观众而言,都十分值得珍藏。
在最终完成的电影中,美术部门往往是不怎么受瞩目的幕后英雄。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华丽的摄影机角度、滤镜的效果和花俏的服装,但是却把电影的视觉质感归为剧本的设计或导演的选择。
导演有可能在筹备阶段的后期才加入项目,电影摄影师可能在开拍前一周才开始做准备,但是美术部门从一开始就在忙活了。与众人商量后,他们需要决定一部电影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
最早为电影拍摄做准备的工作人员中就有分镜画师。本质上,他们负责为一部电影提供蓝图。在此之前,这部电影还只停留在文字形式上。分镜是电影被拍摄出来前具有的第一个视觉化形象。通过和导演的密切合作,分镜画师们把剧本或者剧本中的段落转化成视觉画面。他们偶尔能看见自己的作品直接被搬到了最终的成片里;更多的时候,他们见证分镜的精髓经由各种形式留在了电影中。
回溯分镜的早期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人们在整个“好莱坞黄金时代”里频繁地使用分镜,却不把分镜视为一门特别的艺术。相反,分镜被认为是一种实现艺术目的的手段。一些电影制片厂宣告倒闭和被拆毁的时候,大量珍贵的分镜在清理中遗失了。随机存活下来的分镜如今被保存在档案馆中开云网址,或是为私人所收藏—实在只能各凭天命。
另一方面,大制片厂时代的结束同样意味着作者导演的崛起。这样一来,电影制作的技术被搁置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关注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掌舵手,也就是导演。大多数导演更喜欢谈论作为成品的电影,而不是电影的制作过程,分镜画师永远不会被提及。分镜大多有版权问题,作品的所有权也往往属于制片方。有的分镜你在网上就能看到,但是数量极其有限,而且通常未经授权。
分镜“用完即弃”的性质也害了这门艺术本身。分镜画师们手脚麻利,反应极快,一页一页地迅速出图。无数段落被剪掉,无数创意被舍弃。还有很多分镜画师鲜少创作精致讲究的分镜,因为他们觉得分镜不值得花费太多时间。
但是,分镜显然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迅速赢得了声誉和认可的艺术。得益于分镜在其他行业的应用,人们越来越将其视为艺术作品欣赏,其意义不仅仅是呈现于纸张上的画面而已。尽管寻回被遗忘的分镜十分艰难,你会发现有很多热情的拥护者始终支持这项行动,这其中包括了那些绘制出分镜的艺术家。例如有威廉·卡梅伦·孟席斯(William Cameron Menzies)和哈罗德·米切尔森(Harold Michelson),有门特·许布纳(Mentor Huebner)、舍曼·拉比(Sherman Labby)和亚历克斯·塔武拉里斯(Alex Tavoularis),还有一批顶尖的职业分镜画师,他们才华横溢,如今仍活跃于电影行业。
据说这是英国美术指导威尔弗雷德·辛格尔顿(Wilfred Shingleton)的作品。这些《蝇王》(Lord of the Flies)分镜不大可能来自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1963年翻拍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同名小说的电影,因为该片拍摄于波多黎各,是一部在缺少美术部门和剧本的情况下完成的黑白电影。这些分镜更有可能是为伊林制片厂(Ealing Studios)早期一部停拍的电影绘制的。
分镜的“艺术性”蕴涵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你能够在一页页纸上直观地看到作品之美,但是,只有当分镜画师的技艺为导演提供了从视觉上探索三维电影的途径时,它才有效用。分镜画师是连接导演对剧本的个人理解与现实执行两个层面的桥梁。他们在制作尚未落实前就开始准备,在拍摄开始后的一两周内就离开了现场。如果你翻看一部电影的雇员名单,他们常常只被记载为几百号人里的“3号或4号员工”。
分镜画师采用剧本中的线索,与导演密切合作,然后将所有创意画成连环漫画一般的图像,神奇地再现了三维空间感。有时,导演将草图交给分镜画师们以完成分镜;有时,分镜画师们自己在粗糙的草图中发现了灵感,加以改善,直到它成为你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分镜。这些分镜上通常附有说明,准确地描述了该场戏的摄影机角度、对话等。
除了帮助导演弄清楚他们想要实现什么,分镜画师还需要和各个部门打交道,让各部门负责人可以构想并且进而落实拍摄中需要的一切东西,从摄影机、灯光设备到特技、假肢和CGI,甚至还有布景。即便导演从一开始就准确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分镜也可以作为工作提示和演示模板使用。
然而,我们在谈论分镜的时候,既要将分镜和简笔人物图区分开来,也要和所谓的“电影美术”(production art)或“概念艺术”(concept art)区分开来,这一点很重要。在今天的电影工业中,电影美术或者概念艺术是一种美术概念图和场景设计工具,几乎全是由电脑制作的全彩画面,提供视觉关键概念和灵感。而简笔人物图通常会交到分镜画师手上,他们再据此创作。
这是海因·赫克罗斯(Hein Heckroth)和艾弗·贝多斯(Ivor Beddoes)所作的一张《红菱艳》分镜草图。两位艺术家用分镜画出了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和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执导的《红菱艳》(The Red Shoes,1948)中整整十七分钟的芭蕾舞场景。
即便如此,这本书确实包含了一些可能会被归为“概念艺术”的分镜,尤其是那些黑泽明在数十年前为《乱》(1985,第176—179页)创作的非同寻常的分镜,也收录了约翰·博克斯(John Box)为《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1962,第68—69页)绘制的分镜,是为了说明这门工艺当时在英国的发展状况。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分镜,像是英国艺术家克里斯托弗·霍布斯和德里克·贾曼(Derek Jarman)合作,为《卡拉瓦乔》(Caravaggio,1986,第142—147页)设计了概念、分镜二合一的作品。尽管《红菱艳》(第56—61页)的分镜明显是一组插画,但它同样以纯粹的分镜形式构建了电影中的场景,以至于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在拍摄中直接将真人素材插到动态分镜(animatic)中。事实上,像海因·赫克罗斯为《红菱艳》画的这种分镜很容易让人想起威廉·卡梅伦·孟席斯的作品。孟席斯绘制的《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1939,第22—25页)分镜,让分镜首次走进真人电影领域。
这本书里所有其他的分镜是更标准规范的分镜,有明确的画幅比。它们并不用于所有镜头,而是为了调度更繁复的镜头段落绘制的。在实际拍摄中,这些段落执行起来往往十分复杂,可能需要动用特技、特效,或者多台摄影机合作。分镜图的性价比很高,可以向资方或电影公司展示,让他们放宽心、慷慨解囊。分镜还能使讨论重头戏的过程变得更为生动有趣。看看《雨人》(Rain Man,1988,第124—125页)中“谁是一垒”(Whos on First)这一段的分镜。这个段落不断重复,贯穿了巴里·莱文森(Barry Levinson)的整部电影。分镜的绘制在电影制作最初始的环节就开始了,最终的成品会被钉在一块大板子上,放在拍摄现场。由于分镜展示的是某个特定的段落,所有的剧组成员都能够直观地看到自己负责的内容以及拍摄进程。(在那些不按时间顺序分段落或分场景推进的拍摄中,分镜的作用尤为重要。)
导演布赖恩·辛格(Bryan Singer)和演员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在看《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2008)的分镜。
正如导演特里·吉列姆在提及他为《妙想天开》(Brazil,1985,第138—141页)和《终极天将》(The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ausen,1988,第148—149页)所绘制的分镜时所说的那样:“它们……是我在一片混乱中可以依赖的东西。有了分镜,我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拍什么,不至于手忙脚乱。”
随着电影拍摄走向数字化,能为分镜画师所用的工具也越来越多了。不出所料,外界普遍认为分镜画师们现在都使用电脑程序工作。事实上,大部分艺术家们依旧倾向于先用铅笔和纸作画,再通过影印的老办法得到高对比度的图像。他们说,在追求速度和精确度上,没有比这更管用的了。这些画作随后会被扫描到电脑上,进一步完善,形成预演(Previz)等过程中会用到的基础材料。预演往往能够用电脑渲染出一部电影的复杂设定,在如今的电影行业中频繁使用,涉及特效和高预算的电影更是如此。
成为分镜画师需要特殊的才能。绘画能力当然位居第一,但第二种能力也同样很重要,即拥有好灵感的同时能够在紧密的团队合作中传达和执行这些想法。
一个优秀的分镜画师需要有在脑海中形成电影画面的能力,其中也包括想象如何进行拍摄。因此,分镜画师得知道摄影机是怎么运作的,这很重要。除此之外,还要了解画面构图、镜头连续性、特效镜头的机制以及特技。画师要懂得分析剧本,才能分解剧本。因为分镜画师们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工作保障,通常也没有经纪人,所以分镜工作既是一门独特的手艺,往往也是一份不稳定的工作。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所熟知的分镜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华特·迪士尼公司改进的(尽管我们能肯定有相当数量的默片在制作中也使用了分镜,可惜的是没有材料保存下来)。约翰·凯恩梅克(John Canemaker)的《纸上的梦想:迪士尼分镜艺术和艺术家》(Paper Dreams: The Art and Artists of Disney Storyboards)中提到,在制作最初的卡通短片时,人们用一些漫画式样的草图作为《蒸汽船威利》(Steamboat Willie,1928,一部七分钟的黑白动画短片,标志着米奇和米妮的首次亮相。它也是第一批使用同步声的动画电影中的一部)等最初的卡通短片的制作基础,这些草图就是最早的分镜雏形。迪士尼的动画师韦布·史密斯(Webb Smith)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工作于迪士尼的故事部门,是他想到了把画出来的场景钉在一块板上、按顺序讲述故事的主意。
分镜画师在动画电影制作中居于十分特殊的核心地位,这一点远不同于真人电影作业。动画电影制作中通常没有完整的剧本。故事和人物塑造先由故事部门的主管与分镜团队完善,然后才投入动画制作,他们肩负着编排人物、情节,尤其还有创作笑料的重大责任。由大规模动画工作室制作的长片里,会有多达三十名分镜画师共同参与“故事决策会”。真人电影制作一般只动用两到三名分镜画师,他们将各自负责不同的场景,人数会因制作规模以及电影涉及的特技和CGI技术适当增加。
这本书聚焦于动画电影中风格各不相同的例子。尤其是戴维·拉塞尔为《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 Framed Roger Rabbit,1988,第154—159页)绘制的分镜,这部真人/动画结合的电影被认为改变了动画长片的命运。尼克·帕克为《超级无敌掌门狗:引鹅入室》(The Wrong Trousers,1993,第160—167页)创造了扣人心弦的高潮,其精彩程度不言自明:一切都画在纸上了。更值得称道的是,那整个段落都是由帕克独自制作的。
韦布·史密斯和他的艺术家同伴们在迪士尼工作室中设想出来的作业系统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其他好莱坞大公司也紧接着采用了这个新方法。到了1939年,巨制《乱世佳人》横空出世。这是当时好莱坞史上制作规模最大的电影,所费不赀。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果断地做出了选择,他认为革命性的彩拍摄以及启用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费雯丽(Vivien Leigh)担当主演对电影而言至关重要。他为威廉·卡梅伦·孟席斯设立了“美术总监”(production designer)这一职位,雇用孟席斯为电影设计视觉效果并且绘制关键段落的分镜,其中就包括了“火烧亚特兰大”。这场戏后来由孟席斯亲自执导。多亏了塞尔兹尼克坚决地保留了当时的图纸,这些分镜稿和《爱德华大夫》(Spellbound,1945,第26—29页)中独特的视觉设计稿才得以幸存下来。
二战后,分镜的运用成了常规,分镜画师在整个好莱坞黄金时代活跃于各电影公司的美术部门开云网址。福斯(Fox)、雷电华(RKO)、米高梅(MGM)、派拉蒙(Paramount)和华纳(Warners)这五大电影公司中的美术部门所拥有的权力可不容小觑。尽管你很难想象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或者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会乖乖听从灯光师的吩咐,但据说,导演们只是来到拍摄现场,按部就班地把摄影机放在指定的地方而已。你可以在本书的第36—47页《万里追踪》(Man Hunt,1941)、《夜长梦多》(The Big Sleep,1946)的分镜里看到这种别样的、黑风格十足的作品的例子;你还会看到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失落”的杰作《安倍逊大族》(The Magnificent Ambersons,1942,虽然人们依旧可以看到这部电影,但永远看不到威尔逊原本想呈现的画面了)那令人扼腕叹息的分镜。
“悬疑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在拍摄现场并不那么喜爱悬念。他十分依赖分镜,以至于他有了在拍摄时完全不看取景器的名声。情况显然不只是这样,你在书中看到的这些分镜,都是对拍摄内容的精准描绘。希区柯克的《爱德华大夫》也许是作为艺术形式的分镜中最著名的例子。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请来了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为这部电影中重要的梦境段落提供了我们现在称之为“概念艺术”的设计。(希区柯克和塞尔兹尼克关系比较紧张,还好有威廉·卡梅伦·孟席斯整合那些“分镜”。)
到了1960年的《惊魂记》(Psycho,第30—31页),“视觉顾问”索尔·巴斯(Saul Bass)为电影中的浴室段落逐镜提供详尽指导。巴斯以为电影中著名的段落做出创造性贡献而闻名,他还为《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60,第72—73页)和《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1961,第74—77页)的几场戏绘制了分镜。好莱坞业内另一位伟大的美术指导哈罗德·米切尔森为希区柯克绘制了《群鸟》(The Birds,1963,第32—33页)的分镜。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杰出的作品,以“分镜之王”门特·许布纳为《最长的一天》(The Longest Day,1962,第78—79页),以及亨利·巴姆斯特德(Henry Bumstead)为《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1962,第80—83页)绘制的分镜为代表。
准确来说,所有分镜画师都是艺术家。分镜画师这项职业并没有特定的职业道路,尽管他们的工作内容通常包括了插画师、平面设计师、图像小说家或者动画师的职责。他们大多数接受过艺术学院的专业训练,但也有很多人是自学成才的。他们才华横溢,富于表现力,性格往往十分外向。他们因电影制作本身具有的协作性质而享受这个过程,因此没有选择从事美术行业的其他工作。当人们忽视他们的精彩作品、整场戏地剪掉分镜,或者认为一张接一张的速写依然不对的时候,分镜画师还不能生气。
人们认为,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星球大战》(Star Wars,1977,第88—95页)标志着现代大片的起点[尽管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大白鲨》(Jaws)早在1975年就率先解决了许多问题]。众所周知,画家拉尔夫·麦夸里(Ralph McQuarrie)和乔·约翰斯顿(Joe Johnston)为卢卡斯的电影宇宙提供了概念图、分镜和角色设计,工业光魔(ILM)负责具体执行。本书含有约翰斯顿绘制的分镜,为卢卡斯太空歌剧的开场段落提供了制作指南。美国电影业就此迎来了一个充满创新和活力的时期,大银幕上出现了许多风格各异但同样令观众兴奋不已的电影,比如《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第96—103页)、《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1980,第104—113页),以及由《夺宝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第114—123页)开启的印第安纳·琼斯电影系列。
导演克里斯·韦奇(Chris Wedge)在看《冰川时代》(Ice Age,2002)的分镜。
这本书后面的部分还会介绍法国和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分镜。这些国家最近才频繁使用分镜,作为一种沟通(更多的是省钱)的工具。那些快速适应分镜并把它当作执导工具的导演们往往也偏爱大场面的想象,像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第180—183页),或者墨西哥导演吉列尔莫·德尔托罗(第188—193页),后者同时在西班牙本土与好莱坞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随着电影步入千禧年,雄心勃勃的电影人们怀揣着似乎难以实现的艺术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借助分镜。艺术家简·克拉克从视觉上为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第206—211页)的广阔世界打造了坚实的地基;同样,戴维·拉塞尔也为纳尼亚系列(第218—221页)、坦普尔·克拉克为已故的安东尼·明格拉(Anthony Minghella)执导的《冷山》(Cold Mountain,2003开云网址,第198—205页)绘制了分镜。
在阅读接下来的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记住阿德曼公司资深分镜画师迈克尔·索尔特的一句话:“人们很容易被漂亮的分镜吸引,但我们的原则是不要沉溺于细节,而是重点把握空间和角度,让分镜足够松散和粗糙。”类似的警告还包括,绘制分镜所需的技艺不是为了让作品最后能在一本叫“××的艺术”的书(比如本书)上显得精美好看,而是为导演和电影服务。许多特别版本的蓝光和DVD影碟会将分镜与电影成品放在一起比较,这向来是个值得留意的内容,人们能从中进一步了解分镜这门艺术。
书中最后一套分镜来自吴宇森的《太平轮》,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电影仍处于制作阶段。这部巨制在2013年拍了一整年,对于一部拍摄于上海与台湾两地的亚洲电影来说,高达三千万美元的预算实属罕见。该片聚焦于中国抗日战争以及中国内战期间著名的太平轮沉没事件。吴宇森本人出了名地不爱用电脑,这些为他绘制的分镜不仅用来实现剧组成员间的沟通,还用于说服投资人以及潜在的客户,向众人展示电影的视觉蓝图。因此,正如你在这本书里看到的,画面并不能代表分镜的所有艺术价值,分镜的实际用途也比你能想象的更为重要。换句话说,除了起源于“米老鼠”,分镜和“米老鼠”真没什么关系。